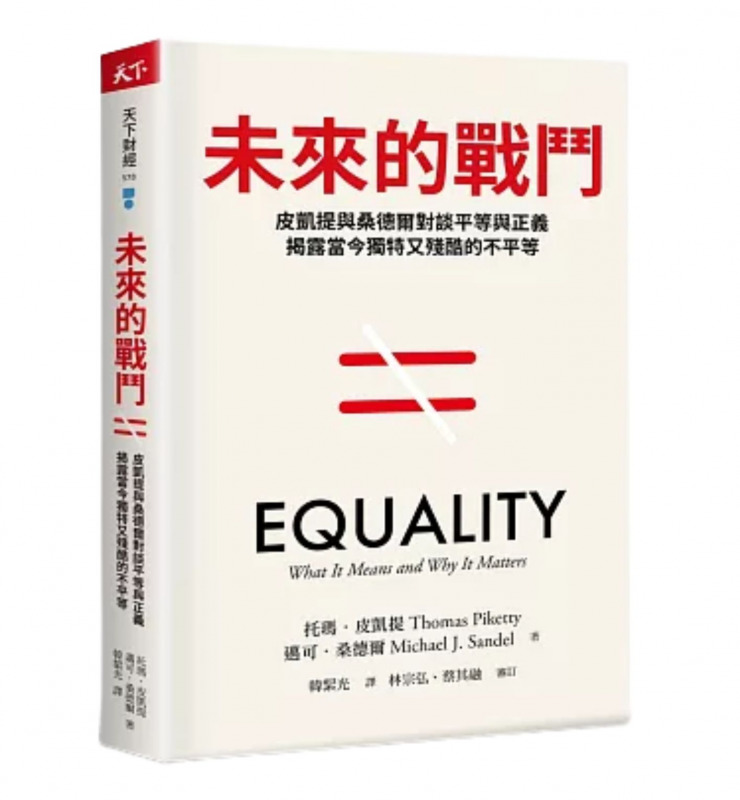
書籍介紹
撰稿/本會研究助理 羅澤
簡介
本書為皮凱提與桑德爾針對不平等議題的一場對談所摘寫而來。皮凱提(Thomas Piketty)是當代最具影響力的經濟學家之一,現為法國社會科學高等學院主任,也是倫敦政經學院國際不平等研究中心教授。他以《二十一世紀資本論》一書在全球掀起貧富不均的論辯,並提倡全球累進財富稅等政策來解決不平等問題;桑德爾(Michael Sandel)則為是哈佛大學政治哲學教授,他在哈佛開設的通識課程《正義》曾一學期吸引超過千名學生註冊,多次成為最受歡迎課程,被改寫成書及製作成線上公開課。大西洋兩岸的兩位大儒將如何看到不平等議題?讓我們透過一篇介紹扼要的一同探索他們的思想。
界定戰場
我們先來看看這兩位大師如何劃定「不平等」這個概念在現實中的具體象徵。桑德爾從三個層面探討平等議題:經濟面強調基本生存的平等權利;政治面著重於政治平等,包括參與決策的權利和取得權力的機會;社會面則關注尊嚴的平等。針對這些面向,他提出了四項具體解決方案:首先是將選舉公共化,禁止私人政治獻金;其次是加強監管政治影響力,如遊說活動,以限制資本主義與政治的連結;第三是引入隨機性機制,如入學與國會代表的抽籤制度;最後則是推動福利國家,朝向社會民主思想轉型。這些方案引發了一個深層思考:為了追求平等,我們該在多大程度上限制自由?
皮凱提則透過歐洲經驗提出了幾個重要觀察:就貧富差距而言,與百年前相比已明顯縮小,從長期來看,平等確實是一個發展趨勢。然而,當前面臨的關鍵挑戰包括如何在維護平等的同時兼顧繁榮與包容,以及如何解決教育系統中的精英主義問題。此外,在南北對抗方面,北方國家憑藉高科技在知識經濟中占據優勢,進而形成了傳統上國際關係學界所描述的「依賴理論」現象。
經濟商品化與財富重分配
社會民主:集體共榮的可能
在自由市場的概念下,要針對不平等做出校正,討論的核心主要圍繞在兩個面向的平衡:經濟商品化(可以交易的品項範圍)與財富重分配(可以擁有的購買力程度)。(當然,還可以討論對個人所有權的限制程度,但暫且擱置)皮凱提以社會民主起手,認為這將是這個時代應該要奉行的思想,並以歷史經驗為基,主張無論是像英國是以憲章運動逐步推動改革,而又或者如瑞典在社會民主黨執政時期的大刀闊斧,兩個國家的改革經驗歸納出三個共同點,改革都展現:首先是將教育系統與菁英主義和資本主義脫鉤,其次是致力於將經濟和社會生活去商品化,最後則是實施高稅率等財富重分配政策。值得注意的是,在蘇聯解體後,社會民主不再被視為完美無缺的理想,並分化出多種流派。皮凱提即在此進一步比較了參與式社會主義與民主式社會主義的差異(見附表),並特別強調:
去商品化如果實現得夠特底,金錢上的不平等就會幾乎變得無關緊要。(p.62)
雖然皮凱提對去商品化表現出較強的偏好,但他認為去商品化與財富重分配應該並行。他進一步分析了社會國家(social state)的概念,指出其範圍應較福利國家更廣,去商品化程度更高,將公共建設和教育納入國家保障範圍。
許多國家在提高社會民主程度後反而促進了繁榮發展。以美國為例,1930-1980年間最高所得稅率達82%,但同期美國的經濟生產力位居世界之首。這主要歸功於教育普及率的提高——透過社會資源重分配來健全教育系統,進而優化整體社會。同樣重要的另個議題是勞工的能動性和政治影響力。若勞工影響力不足,可能導致上層階級擁有權力與資本卻無需負責,最終造成社會分裂。
筆者認為,從永續發展的角度來看,如果教育資源過度集中,將導致人才培養失衡:只有少數精英能接受優質教育,而中下階層的教育品質低落。這種情況最終會導致國家僅靠越來越小的精英圈支撐,實在有違民主精神。因此,所謂英才教育(meritocracy)究竟在本質上如何與民主相符,實在有論理上應當彌補之處。
過度商品化存在兩個問題:一是大家會更看重錢,窮人更難取得所需資源;二是錢滲入各領域,會敗壞財貨或服務的本質,讓原本出於良善動機的利他行為愛質。(p.70)
皮凱提也提出了一個具體例子:若根據學生成績表現給予教師薪資獎勵,這可能不會真正提升教育品質。舉例而言,在醫療領域,儘管美國私人醫療體系為從業者提供高薪,但該國的平均壽命和基本健康指標表現卻不理想,相較之下,歐洲醫療從業人員雖然薪資較低,但整體醫療成效更佳;在教育領域中,皮凱提同樣反對高等教育的商品化趨勢,並指出就算是最昂貴的常春藤盟校也並非營利機構。他進一步主張,去商品化應擴及文化、交通等眾多產業領域。
此處可以思考的是,在現今的教育體系中,許多學生為了考試而讀書,失去了學習的本質意義。教育被簡化為謀生技能的培養工具。但教育是否要與謀生脫鉤?如果造成更高程度的剝削又該怎麼辦?此時政治面、社會面的平等,是否會與經濟平等的考量相衝突?
價值衡量:效益主義與道德律?
筆者在此延伸上文,讓我們我們思考一個問題:當我們摒棄效益主義的評量標準(如標準化測驗或業績考核)時,要如何評估教育品質?(同樣的思考脈絡出現在本書頁78)以桑德爾舉的例子,亞當・斯密認為應該根據學生出席率來決定教授薪資,也質疑這類量化標準可能會破壞其本質。但反過來說,如果完全沒有標準化的評量機制:
- 如何向決策者證明教學成效?
- 當學生對教學品質提出投訴時,該用什麼標準來判定?
- 如何客觀評估教師是否應該續聘或撤換?
效益主義雖然可能違背教育的道德價值,但如果再加上理性主義以及量化方法(如當代盛行的大數據),其實提供了可預測性和相對客觀的標準,這種邏輯系統對於大眾來講更具說服力,而且減少了主觀判斷的需求,提高了規則的通用性。這部分的討論,不但沿襲上面所說的「菁英與大眾的對抗」,也可以在向下延伸探討民粹的本質。我們先就此打住,回歸到書中關於價值衡量系統的內容,皮凱提就此提出了幾個重要觀察:
- 多數仍以生產成本為主要考量
- 所有計算標準都有其局限性
- 不完全取決於市場供需,而受公共化和法律影響,故衡量價值仍是政治過程。
由此可見,「去商品化」本身其實也包含了政治價值衡量和批判性評估,可在主觀判斷和客觀標準間取得平衡。然而,現況比理論想的還嚴重,因為即使不開始進行去商品化,目前醫療和教育資源投入也已然停滯,皮凱提劍指美國高教投資:
現今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已經大幅提高,但我們投入教育的資源卻人停滯在1980-1990年代的水準。(P.81)
僅有少數精英學生能獲得豐富的教育資源之時,大多數學生的資源就相對不足,這會降低社會民主所需要的集體決策品質,因為參與程度不足會導致決策權力的失衡。以勞資談判為例,當資源分配被限制在供需法則下時,資本主義與民主化產生互斥:由於資源的依賴性,弱勢群體難以獲得平等的決策權,同理可見於南北對抗的情境。
反動:以民粹對抗新自由主義主義
民粹的基本定位
就1980年代以來的超全球化(hyper-globalization)現象,與透過精英體制(meritocracy)、全球化、金融化三大支柱建構的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兩位作者都持批判態度。皮凱提並指出其中的關鍵矛盾:「批判財貨與資本的跨境流動」與「批判移民政策」之間存在著不對稱性,左派放棄前者而接納後者,右派則反之。
皮凱提首先指出精英主義思想的問題。過去幾本關於精英主義的書都在批判一個現象:成功者過度要求自己,並建構一套正當化自己享有社會資源的思想體系。從左派陣營(包括美國民主黨政府)的政策可以看出,他們一方面加強累進稅制,另一方面又大力推進全球化和貿易自由,將財富重分配與資本流動負向連結,但從川普和歐洲的發展可以看出,左派的過度認同導致了反效果。至於這種媒體常冠以「民粹」之名的反效果,兩人對於民粹主義的本質有所歧見。皮凱提先將其區分為兩種:
- 左派式民粹:以民主社會主義為主要訴求(桑德斯)
- 右派式民粹:以民族主義、本土至上、反移民為主(川普、勒朋)
無論是左派或右派的民粹主義者,都傾向反對自由市場全球化。雖然他們的理念不同,但結果相似。桑德爾指出,美國的民粹主義起源於19世紀太平洋鐵路建設時期,當時人們開始試圖從東北部財團手中奪回對鐵路及其延伸產業的控制權,從後續歷史發展可以看出:
人們對抗權貴和本土主義這股思維,在歷史上一開始就是交織在一起 。(p.94)
他認為民粹主義的興起反映了社會民主政治的失敗,暴露了左派的不足之處。最關鍵的例子是歐巴馬在面對金融危機時,不得不讓納稅人承擔銀行紓困的成本來拯救國家金融系統。這引發了一個深層思考:民主社會雖然允許人們對幸福生活有不同的詮釋,卻試圖建立一套中立的評量工具,市場機制並非真正客觀中立,其中必然涉及政治價值判斷。過度依賴可量化的市場邏輯,反映出對民主審議制度的恐懼。害怕什麼呢?害怕我們沒有辦法透過民主審議來決定,市場的自由到底可以擴張到什麼範圍。
所以,桑德爾在這裡特別點出了一個可以闡明的細部差別,也就是民粹主義的核心並不是財富重分配,而是要從傳統上的精英手中奪回權力還給民眾。這源於什麼呢?經濟不平等,財富分配只是因為無法直接奪回權力,因為權力繫於資本,所以只好透過重分配資本來奪回權力。
若去商品化成功,是否能減緩民粹主義?根據前述分析,若民粹主義的核心目標是權力分配而非財富重分配,那麼去商品化可降低資本與權力的連結,並減少其對政治的影響。這個假設是否符合桑德爾的理論詮釋,值得進一步驗證。
菁英體制與分配正義
桑德爾接著探討了我們熟悉的精英體制問題。這種體制造成了嚴重的社會對立,但弔詭的是,這種對立反而被用來正當化現有的公共制度和法律秩序,使得「成功」被完全個人化。精英制度強調能力至上,不僅加劇了社會分化,還經常勸告底層民眾要「努力向上」來解決不平等問題,「推崇贏家、譴責輸家」的觀念已深植於新自由主義之中。
或許也是因此,當基層民眾與上層階級對立時,他們把精英思維和全球化視為一體,這種詮釋可以解釋上文桑德爾所述現象。桑德爾提出教育入學與政治選拔的隨機抽選制度。他主張從符合基本資格的候選人中進行抽選,類似陪審團的選拔方式。這個制度有三個優點:
- 提醒人們成功具有隨機性
- 減少資本對選拔過程的影響
- 促進多元化,符合民主精神
皮凱提回應提到了馬可維茲的觀點:以結果論的角度來看,只要能達到預設的平等標準(如低收入家庭入學比例),過程如何並不重要。這與桑德爾強調手段和過程的想法形成對比。這帶出了一個值得深入討論的問題:是否有比抽選制度更好的方案?結果導向的方法可能在達成平等目標上更有效,但我們需要在效率和公平程序之間取得平衡。
菁英體制之所以如此具有說服力,最簡單的原因在於社會上明顯的薪資收入差距。社會在教育資源分配上對技職教育的投入相對較少,這種制度實際上已經有點倒果為因預設了勝負,用透過不同的薪資與教育資源水準,向基層勞動者傳達了一種暗示:你的工作較不具價值。也正是前面所提到的一種道德判斷。
而對於這種體制的運行結果,就是貧富差距。雖然依定程度的貧富差距幾乎可以說是必然,但當這種差距已然過度擴張,就不單單是金錢問題,而是代表富人可以購買他人的時間,這是來自於私有化財富無上限累積所產生的尊嚴問題,皮凱提對此有三主張:
- 應當設立最低工資
- 應當設立最高工資
- 應當採用嚴格的累進稅率制
桑德爾則進行補充,主張累進稅制與分配的道德基礎不能與認同感與其背後所象徵的社會意識脫鉤,這也是他為何批判羅爾斯的差異原則——因為無知之幕背後並沒有描繪一套其所認同的、善的生活方式。換言之,這種尊嚴問題帶來的惡劣影響,很大程度就是不同階層的人們之間會失去共同的社會生活,這種現實的割裂會加劇社會對立,而無知之幕並沒有解決這種問題,創造一種共同的歸屬感。
兩者在此出現一個交鋒:雖然都認同社會價值(文中稱「共同性」)與累進稅制的交互作用,但桑德爾似乎更偏好以前者為基礎,至於後者則需在推動前者的同時一起跟進,皮凱提則挑戰此一論理,隱約指出此一論理方式並不恰當,並顯然更偏好以累進稅制作為改革主力。至於這種傾向從何而來?筆者推測是因為皮凱提已然洞悉固有體制內已然僵化的、在菁英體制下的價值觀念,他點出,左派們所發展出的國際公共制度,如當前國際社會所運行的、極其複雜的國際法制,恰是歷代政府精英提供給富人們,使之得以規避責任最佳的正當化工具:
我們建立起一套國際法制,基本上讓大富豪得以完全規避公民責任,然後我們還得假裝這很正常。(p.159)
結語:在制度約束與個人自由之間
在作結之前,筆者得先稍稍批判這本書的譯名。本書原文名為 Equality: What It Means and Why It Matters ,當然,譯者明顯試圖強調一件事:不平等將是未來各方研究的重要核心之一。但這樣的翻法卻把最重要的平等拿掉,反而沒有把象徵意涵(means)跟重要性(matters)帶入,更忽略了一件更關鍵的概念:不平等從來都不是「未來的戰鬥」,人們從古至今,都不斷在多元的光譜上思辯「平等」,這是一場過去的、現在的、未來的戰鬥,「不平等」會橫跨時空,在不同時點與我們相遇。
桑德爾與皮凱提的討論奠基於許多學術基礎之上,不過作為一場對談的精華,在深度上依然有限。當然,我們還是可以歸納出一些脈絡:
- 要實現真正的平等,必須同時從經濟、政治和社會三個層面推動改革,單一面向的變革難以奏效。
- 社會民主為改革提供了可行路徑,關鍵在於在商品化程度與財富重分配之間尋求最佳平衡點。
- 精英體制雖標榜能力至上,實則加劇社會分化,更常被既得利益者用來合理化不平等現象。
- 平等的實現不僅需要制度改革(如累進稅制、最低工資),更需要建立起強韌的社會共同體意識。
追求平等不只是經濟與政治制度的改革工程,更需要我們重新審視並重塑社會價值觀與道德判斷。這是一項需要全民參與、持續投入的長期工程,在制度約束與個人自由之間,需要的不僅是政策思辯,更多的是,我們這一個世代,要如何定義群我關係,以及背後所隱含的人文價值。
附錄
| 特徵 | 參與式社會主義 | 民主式社會主義 |
|---|---|---|
| 經濟模式 | 參與式計劃,無市場或中央計劃 | 混合經濟,市場+國有化+福利 |
| 民主形式 | 直接民主,去中心化 | 代議制民主,中心化 |
| 對資本主義態度 | 徹底取代 | 改革與共存 |
| 實踐範圍 | 理論為主,小規模實驗 | 廣泛應用(如北歐、拉美部分國家) |
| 挑戰 | 規模化與效率問題 |
資本反對與改革局限性 |
另可參考:https://ancillaryreviewofbooks.org/2025/03/12/hail-the-horizontal-review...
